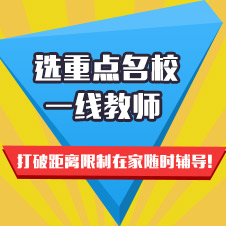散文的“散”與“文”
作者: 朱向前 來自: 《大眾日報》
散文是個大題目,我個人的感覺是:讀得愈多就愈不知道說什么好,或者說,就愈講不清散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仔細琢磨琢磨,又發覺光是這“散文”二字就有點說道,而且似乎還可以分而說之。
先說其“散”。
為什么叫“散文”?先哲就有“散文就是和友人松散地聊天”,“散文就是思想的散步”,“散文就是散漫的文體”,“散文就是自由”云云。種種說法,多不離一個“散”字。在我看來,這個“散”字強調的是散文家的本色的輕松,自然的流露。因為散文既沒有詩歌的韻律和節奏,也少有小說的情節和故事,它主要不依靠“行頭”來支撐和夸張自己——不要堂皇氣派的西裝革履,也不要珠光寶氣的晚禮服,它只是身著泳裝松散隨便地走向海灘,在陽光下裸露真實的胴體。正所謂“是大英雄自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如此說來,一篇散文的好壞和它的形式技巧的干系反倒不大了,而主要取決于它是否有一個天生麗質的“真身”。有,則嬉笑怒罵皆成佳構;無,則忸怩作態終是廢話。只是這“真身”涵蓋甚廣,它包括一個人的才情、學養、個性氣質和人生歷練乃至眼光、胸襟與品操等等。簡言之,散文是一個人的全面展示,一個散文家的修煉過程,也就是一個“人”的修煉過程。人生不到一定的境界,是不大容易作出真散文來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同意這樣一種說法:詩歌是屬于青年的,而散文更屬于中老年。因為,前者需要一種如火的激情,而后者則需要一種如水的心境。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人入世漸深,經歷了幾番人世滄桑之后,開始把很多物事推遠了,看輕了,看淡了,進入了一種散淡如菊、我心悠然的澹泊與超脫的境地,才有可能獲得一副審美的心情與眼光,從而寫出真正耐得咀嚼的韻味悠長的美文。
就像大自然,只有告別了春天的繁華熱鬧,褪去了夏天的炎熱躁動,才能迎來秋天的天高云淡、寧靜致遠一樣;亦如太極高手,內心深厚卻從容不迫,沒有了虎氣,沒有了獅吼,只剩得了鶴步的悠閑。故爾,我們讀中年以后的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就更能體會“愈老的姜愈辣”這句話的內涵了。就以當前文壇論,幾位作散文的好手也大都年逾不惑,才見出爐火純青的火候。無論是余秋雨的底蘊豐厚,還是張承志的沉雄蒼涼,也無論是賈平凹的清淡古雅,還是周濤的氣勢恢宏,莫不可作如是觀。從此一角度看,散文對于青年人來說,倒未見得是一種十分相宜的文體。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辯證法無處不在。恰恰因了散文的隨意,親切和短小,它就和詩歌一樣,往往最容易受到那些鐘情于文學的年輕人的青睞,或者說,他們選擇散文作為自己尋覓通向文學殿堂的最初的小徑,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也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這就有點“兩難”了。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散文文體的散漫和輕松而言,它于初學者甚為相宜;從散文文心的散淡和悠遠而言,它于年輕人又不甚相宜。對于青年人的選擇和愛好誰也無可厚非,而至于散文自身的要求誰也無法強求于人。人生是一個一個日子累積起來的,所謂“少年老成”也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年齡和閱歷都有待時空的發展,不是單憑主觀努力所能一蹴而就的。但是還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對一個有心追求真散文境界的人來說,他必須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緊緊抓住文化的修養而不放松。于此就說到了第二個字:散文的“文”。
“文”者,文化也。它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但又確實是具體而微,可見可聞的。小到一花一木一沙一石,大到天空海洋等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社會萬象和人心百態,無不浸**著文化,表現著文化。尤其當它們出現在散文中,就更會展示出一個作者文化的修養、功底和眼光,所謂文格之高下,文心之雅俗,文筆之精粗,在明眼人看來是纖毫畢現難以藏拙的。如果說,到了一定程度,小說創作依然可以相當地倚重于操作技巧和個人經歷等有關因素,那么,散文創作則愈往后就愈能顯示出文化和學養的后勁。極而言之,散文的比賽就是文化的比賽。
舉例來說,當前文壇的“散文家散文”和“學者散文”兩派創作之消長態勢便是“比文化”的必然結果。所謂“散文家”一派,我指的是新時期之初就以散文創作步入文壇且十數年來一直專事散文寫作的一批中青年散文家,他們一度成為散文界的主力,為新時期散文的活躍與繁榮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他們如今多已步入中年,按說是理應進入散文創作的“秋天”,寫出臻于化境的杰構佳什。但事與愿違,這樣的角色不多,反倒有相當多的“散文家”給人的印象是變得越來越不會寫散文了。沒有情趣,沒有見識,沒有了青年人的激情,也沒有過來人的老到,僅有的一點“文采”也被當今的“泛文學化”——比如在數年前堪可當作散文詩來讀的文辭華麗的廣告——所徹底消解了。粗略檢討起來,這大致可以歸結為文化準備上的先天不足所導致的一種內虛現象。
與以上現象恰成強烈反差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以來,一批學者從鈄刺里殺入散文界,立即帶來了一股濃濃的書卷氣息,哲思意味和高雅情調,使廣大讀者為之傾倒。他們中的多數人幾年前也許還無意于創作,更不存散文家之想,但不經意間卻涉筆成趣,出奇制勝,真是無心插柳,歪打正著,短短時間內或自創一家,或蔚成大國——老一輩的如張中行、金克木、中年的如余秋雨、雷達,青年的如周國平、陳平原等等。他們的“客串”改組乃至改變了當代中國散文的面貌。其中尤為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余秋雨教授,他的文化散文幾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國文化的凄風苦雨和中國文人的集體痛苦感,再以個人生命的真體驗和真性情澆鑄成文字,舉重若輕,上承新文學散文之余緒,為整個當代散文的創作開出了一片新風景。
學者散文的奇觀,其成因當然不僅在文化這一面,但文化上的厚積薄發卻不能不首先為人們所注意。其實,推廣開來看,這不單單牽涉到散文創作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當代文學的深化與發展。文化準備不足的后遺癥在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中或已經或正在或將要暴露無疑,只不過通過“學者散文”的崛起,在給了我們一個振奮的同時,更給我們以刺激,以警醒: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亡羊補牢,猶為未晚。
扯遠了。
話再回頭說散文的“散”與“文”——無散淡心境不易作出真散文,然,散而無“文”則行之不遠,亦不足道哉。
散文是個大題目,我個人的感覺是:讀得愈多就愈不知道說什么好,或者說,就愈講不清散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仔細琢磨琢磨,又發覺光是這“散文”二字就有點說道,而且似乎還可以分而說之。
先說其“散”。
為什么叫“散文”?先哲就有“散文就是和友人松散地聊天”,“散文就是思想的散步”,“散文就是散漫的文體”,“散文就是自由”云云。種種說法,多不離一個“散”字。在我看來,這個“散”字強調的是散文家的本色的輕松,自然的流露。因為散文既沒有詩歌的韻律和節奏,也少有小說的情節和故事,它主要不依靠“行頭”來支撐和夸張自己——不要堂皇氣派的西裝革履,也不要珠光寶氣的晚禮服,它只是身著泳裝松散隨便地走向海灘,在陽光下裸露真實的胴體。正所謂“是大英雄自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如此說來,一篇散文的好壞和它的形式技巧的干系反倒不大了,而主要取決于它是否有一個天生麗質的“真身”。有,則嬉笑怒罵皆成佳構;無,則忸怩作態終是廢話。只是這“真身”涵蓋甚廣,它包括一個人的才情、學養、個性氣質和人生歷練乃至眼光、胸襟與品操等等。簡言之,散文是一個人的全面展示,一個散文家的修煉過程,也就是一個“人”的修煉過程。人生不到一定的境界,是不大容易作出真散文來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同意這樣一種說法:詩歌是屬于青年的,而散文更屬于中老年。因為,前者需要一種如火的激情,而后者則需要一種如水的心境。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人入世漸深,經歷了幾番人世滄桑之后,開始把很多物事推遠了,看輕了,看淡了,進入了一種散淡如菊、我心悠然的澹泊與超脫的境地,才有可能獲得一副審美的心情與眼光,從而寫出真正耐得咀嚼的韻味悠長的美文。
就像大自然,只有告別了春天的繁華熱鬧,褪去了夏天的炎熱躁動,才能迎來秋天的天高云淡、寧靜致遠一樣;亦如太極高手,內心深厚卻從容不迫,沒有了虎氣,沒有了獅吼,只剩得了鶴步的悠閑。故爾,我們讀中年以后的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就更能體會“愈老的姜愈辣”這句話的內涵了。就以當前文壇論,幾位作散文的好手也大都年逾不惑,才見出爐火純青的火候。無論是余秋雨的底蘊豐厚,還是張承志的沉雄蒼涼,也無論是賈平凹的清淡古雅,還是周濤的氣勢恢宏,莫不可作如是觀。從此一角度看,散文對于青年人來說,倒未見得是一種十分相宜的文體。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辯證法無處不在。恰恰因了散文的隨意,親切和短小,它就和詩歌一樣,往往最容易受到那些鐘情于文學的年輕人的青睞,或者說,他們選擇散文作為自己尋覓通向文學殿堂的最初的小徑,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也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這就有點“兩難”了。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散文文體的散漫和輕松而言,它于初學者甚為相宜;從散文文心的散淡和悠遠而言,它于年輕人又不甚相宜。對于青年人的選擇和愛好誰也無可厚非,而至于散文自身的要求誰也無法強求于人。人生是一個一個日子累積起來的,所謂“少年老成”也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年齡和閱歷都有待時空的發展,不是單憑主觀努力所能一蹴而就的。但是還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對一個有心追求真散文境界的人來說,他必須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緊緊抓住文化的修養而不放松。于此就說到了第二個字:散文的“文”。
“文”者,文化也。它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但又確實是具體而微,可見可聞的。小到一花一木一沙一石,大到天空海洋等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社會萬象和人心百態,無不浸**著文化,表現著文化。尤其當它們出現在散文中,就更會展示出一個作者文化的修養、功底和眼光,所謂文格之高下,文心之雅俗,文筆之精粗,在明眼人看來是纖毫畢現難以藏拙的。如果說,到了一定程度,小說創作依然可以相當地倚重于操作技巧和個人經歷等有關因素,那么,散文創作則愈往后就愈能顯示出文化和學養的后勁。極而言之,散文的比賽就是文化的比賽。
舉例來說,當前文壇的“散文家散文”和“學者散文”兩派創作之消長態勢便是“比文化”的必然結果。所謂“散文家”一派,我指的是新時期之初就以散文創作步入文壇且十數年來一直專事散文寫作的一批中青年散文家,他們一度成為散文界的主力,為新時期散文的活躍與繁榮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他們如今多已步入中年,按說是理應進入散文創作的“秋天”,寫出臻于化境的杰構佳什。但事與愿違,這樣的角色不多,反倒有相當多的“散文家”給人的印象是變得越來越不會寫散文了。沒有情趣,沒有見識,沒有了青年人的激情,也沒有過來人的老到,僅有的一點“文采”也被當今的“泛文學化”——比如在數年前堪可當作散文詩來讀的文辭華麗的廣告——所徹底消解了。粗略檢討起來,這大致可以歸結為文化準備上的先天不足所導致的一種內虛現象。
與以上現象恰成強烈反差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以來,一批學者從鈄刺里殺入散文界,立即帶來了一股濃濃的書卷氣息,哲思意味和高雅情調,使廣大讀者為之傾倒。他們中的多數人幾年前也許還無意于創作,更不存散文家之想,但不經意間卻涉筆成趣,出奇制勝,真是無心插柳,歪打正著,短短時間內或自創一家,或蔚成大國——老一輩的如張中行、金克木、中年的如余秋雨、雷達,青年的如周國平、陳平原等等。他們的“客串”改組乃至改變了當代中國散文的面貌。其中尤為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余秋雨教授,他的文化散文幾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國文化的凄風苦雨和中國文人的集體痛苦感,再以個人生命的真體驗和真性情澆鑄成文字,舉重若輕,上承新文學散文之余緒,為整個當代散文的創作開出了一片新風景。
學者散文的奇觀,其成因當然不僅在文化這一面,但文化上的厚積薄發卻不能不首先為人們所注意。其實,推廣開來看,這不單單牽涉到散文創作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當代文學的深化與發展。文化準備不足的后遺癥在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中或已經或正在或將要暴露無疑,只不過通過“學者散文”的崛起,在給了我們一個振奮的同時,更給我們以刺激,以警醒: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亡羊補牢,猶為未晚。
扯遠了。
話再回頭說散文的“散”與“文”——無散淡心境不易作出真散文,然,散而無“文”則行之不遠,亦不足道哉。